门缝里,先看到的是一双眼睛。
并非直接对视,而是先落在晓风臂弯的竹篮上,目光像被磁石吸住,凝滞了一瞬,才缓缓抬起,看向晓风的脸。那是一双老年人的眼睛,眼窝微陷,眼皮有些松弛,但瞳孔却异常清亮,带着一种锐利的、仿佛能穿透表象的审视。岁月在眼角刻下深深的纹路,像是无数飞翔轨迹留下的印痕。
门又开大了一些。站在门内的是个清瘦的老人,头发全白,梳得一丝不苟,穿着件半旧的浅灰色中式褂子,身板挺直。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小小的棕毛刷子,指缝间沾着些细小的羽毛屑。
“什么事?”老人的声音不高,有些沙,但吐字清晰,带着一种不容打扰的疏离。
晓风的心跳得很快,他下意识地紧了紧挎着篮子的手臂,喉结动了动:“您……是海伯吗?我……我捡到一羽鸽子,脚环上有‘海’字。茶馆的张老师说,可能是您的。”
他边说,边轻轻掀开了盖在篮子上的纱布。
老人的目光,再次落向篮中。这一次,晓风清楚地看到,那锐利的眼神在接触到“灰影”的刹那,仿佛被投入石子的深潭,猛地波动了一下。那并非简单的惊喜或激动,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震动,混杂着难以置信、深切忧虑,以及某种失而复得的、沉重的温柔。所有属于老人的疏离和冷淡,在这一瞬间冰消瓦解。
他没有立刻去碰鸽子,甚至没有跨出门槛,只是站在那里,静静看了几秒钟。山风吹过,竹叶沙沙,时间仿佛被拉长了。
“进来说。”终于,老人侧身让开,语气依旧平淡,却已少了那份拒人千里的意味。
晓风跨过门槛,走进院子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微微一怔。
院子比从外面看感觉的要大得多,干净得近乎肃穆。青砖铺地,缝隙里长着茸茸的、极短的青苔。左侧是一片精心打理过的花圃,种着些常见的月季、栀子,却修剪得格外齐整。右侧,则是一排长长的、倚墙而建的鸽舍。
那鸽舍和他想象中完全不同。不是简陋的木笼或鸡棚似的结构,而是用杉木板材搭建,漆成深绿色,分成许多整齐的单元。每个单元前都有木制的落地棚,供鸽子进出栖息。鸽舍正面是细密的铁丝网,里面光线充足,可以看到干净的巢盆、栖架,以及悬挂着的饮水器和食槽。空气中没有寻常禽舍的异味,反而隐隐有一股干燥木材和谷物混合的、洁净的气息。
最引人注目的是,鸽舍上方屋檐下,挂着一排小巧的、已经有些褪色的木质奖牌,以及几个擦拭得很干净的金属奖杯。阳光偶尔穿过竹叶缝隙,在那些奖杯上跳跃出零星的光点。
这里的一切,都透着一股经年累月、一丝不苟的秩序感,以及一种沉浸其中、近乎虔诚的专注。
海伯关上门,闩好,动作不疾不徐。然后他转向晓风,伸出手:“给我看看。”
这一次,晓风没有犹豫,小心地将整个篮子递过去。海伯接过篮子,没有立刻取出鸽子,而是提着它,径直走向院子角落一个石砌的水池边。水池旁有个小木凳,他坐下,将篮子放在脚边,这才用那双布满老年斑却稳定有力的手,极轻柔地将“灰影”捧了出来。
他的动作与茶馆张老师相似,却又不同。更加从容,更加周密,仿佛每一个触碰、每一次翻看,都遵循着内在的、严谨的程序。他先让鸽子站在自己膝头,观察它的站姿和精神。然后一手轻拢鸽身,另一手食指极小心地触碰、按压左翼受伤的部位,他的眉头微微蹙起,专注得仿佛在聆听鸽子骨头细微的呻吟。
晓风屏息站在一旁,不敢出声。他看到海伯检查了“灰影”的眼睛、口腔、羽毛,甚至轻轻捏开尾羽看了看下方的皮肤。整个过程,“灰影”异常安静,只是偶尔喉咙里发出极低的“咕噜”声,像是安慰,又像是诉说。
良久,海伯长长地、几不可闻地舒了口气。他抬起头,看向晓风,目光里的锐利已被一种深沉的温和取代。
“桡骨轻微骨裂,韧带拉伤。万幸,没全断,也没伤到主要关节。”他开口,声音依旧沙哑,却像是在陈述一个经过精密计算后的结论,“你处理得对。静养,没乱动,没乱喂。它口腔干净,眼神没散,底子还在。”
晓风提到嗓子眼的心,稍稍落回去一些。
“它……叫‘灰影’?”海伯忽然问,手指轻轻抚过鸽子背上的雨点斑纹。
晓风脸一热,点点头:“我……我随便叫的。它雨夜里来的,像个影子。”
海伯嘴角似乎极轻微地动了一下,像是一个未能完全绽开的微笑。“名字不错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重新变得深远,“它本来就叫‘影’。‘灰影’,是我三年前作育的,它的父亲是‘闪电’,母亲是‘墨雨’。”他说起这些名字时,如同说起老友,带着熟稔的温度。
“那天风雨太大,训放三十公里,它一直没回来。我找了三天。”海伯的声音低下去,“以为它折在外面了。”他低下头,看着膝上安静依偎的鸽子,手指极其轻柔地梳理着它颈部的羽毛,那紫绿色的光泽在他指间流转。“老伙计……回来就好。”
那一刻,晓风忽然清晰地感觉到,这并非一羽普通的财产,而是这位孤独老人某种情感的寄托,是他漫长岁月里精心雕琢的作品,是与他共享天空与风雨的伙伴。
海伯小心地将“灰影”放回垫了软布的篮子,站起身。“跟我来。”他提起篮子,走向正屋。
正屋是间老式的堂屋,家具简单,一张八仙桌,几把椅子,一个书柜,却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东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,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细线,标记着许多地点和路线。西面墙边立着一个玻璃柜,里面整齐陈列着更多的奖杯、奖牌,以及一些装在相框里的、鸽子在蓝天或领奖台上的老照片。
但最吸引晓风目光的,是北墙书桌上摊开的一本厚重的册子,以及旁边堆放的许多笔记和手稿。册子内页贴满了泛黄的照片,旁边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密密麻麻的注释,还有复杂的系谱图。
海伯将篮子放在桌旁一张铺着软垫的藤椅上,示意晓风坐下。他自己也在一张旧藤椅上坐下,目光再次落在晓风身上,审视的意味重新浮现,但已不带最初的冷漠。
“学生?多大了?”他问。
“刚高考完,十七。”晓风回答,手心有些出汗。
“哦。”海伯点点头,目光扫过晓风洗得发白的校服裤子,“没考好?”
晓风身体微微一僵,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海伯似乎并不在意答案,也没追问,转而问道:“你捡到它,照顾它,又特意找来。为什么?镇西头阿斌,是不是出钱要买它?”
晓风惊讶地抬起头,没想到老人连这都知道。他老实承认:“是,他出一百块。我没卖。”
“为什么没卖?”海伯追问,眼睛紧盯着他。
晓风想了想,努力组织语言:“我……我觉得它不是一件东西。它受伤了,但眼睛很亮,它想活。而且……我觉得它应该回到它真正属于的地方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些,“再说,那一百块……拿了也不踏实。”
海伯静静地听着,手指在藤椅扶手上轻轻敲了敲,半晌,才缓缓道:“鸽子通人性。你待它如何,它心里知道。你救了‘灰影’,这份情,我记下。”
他站起身,走到书桌旁,从那堆手稿中抽出一本薄薄的、线装的笔记本,封面上没有任何字迹。他走回来,将笔记本递给晓风。
“这里面的东西,比一百块值钱。算是我的一点谢意。”
晓风疑惑地接过,翻开第一页。里面是手写的蝇头小楷,工整清晰,内容却让他心头一震:
“鸽性篇第一:夫鸽者,羽族之灵也。其性躁者,难安于舍;其性怯者,易惊于途;其性贪者,易溺于食;其性惰者,难振于翼。故鉴鸽先鉴性,养鸽先养心。心静则鸽稳,性明则途通。鸽之优劣,半在血统筋骨,半在心性气韵。血统筋骨可察可量,心性气韵,唯日久方见。故曰:鸽性即人性也。”
这寥寥数语,如同在他这几日混沌的心绪中,投下了一束强光。他猛然想起祖父那本书序言里相似的话,但这里的阐述,更深邃,更系统,直指核心。
他抬起头,看向海伯。老人正望着窗外鸽舍的方向,侧脸在午后的光线里,显出岩石般的沉静与沧桑。
“海伯,我……”晓风握着那本薄薄的笔记,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来,“我能跟您学养鸽子吗?学这些?”话一出口,他自己也吓了一跳,脸颊发热。
海伯转过头,目光落在他脸上,那锐利的审视感又回来了。他看了晓风很久,久到晓风几乎要低下头去。
“养鸽子,”海伯缓缓开口,每个字都像经过称量,“不是玩物丧志,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去处。它是一门学问,苦得很,也寂寞得很。要耐得住烦,吃得了亏,看得穿得失,还得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还得真心喜欢这些不会说话的羽族。”
他站起身,走向门口,示意谈话结束。“‘灰影’需要专门调理。你的心意我领了。这本东西,拿回去看。看懂了,若还有兴趣,可以再来问我。”
晓风知道,这是送客了。他小心地将笔记本抱在怀里,像抱着什么易碎的珍宝,站起身,对海伯深深鞠了一躬:“谢谢海伯。我……我会再来的。”
海伯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
晓风走出堂屋,再次经过那个整洁肃穆的院子。鸽舍里,有几羽鸽子好奇地探出头来,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羽色和眼神,安静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少年。
走出那扇斑驳的木门,山风和竹叶声再次将他包裹。门在身后轻轻合上,隔绝了那个充满秩序与专注的世界。
晓风站在门外,怀里揣着那本笔记,臂弯里空荡荡的,却感觉心里被塞进了什么沉甸甸的、又充满光亮的东西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青砖围墙和墙头摇曳的竹梢,然后转身,沿着来路向镇子走去。
脚步比来时,轻快了许多。
院门内,海伯没有立刻回屋。他站在鸽舍前,看着篮子里安静休息的“灰影”,又抬眼望向晓风离去的方向,许久,低声自语了一句,随风飘散:
“三分之差……羽间之缘。小子,路还长着呢。”
(第四章完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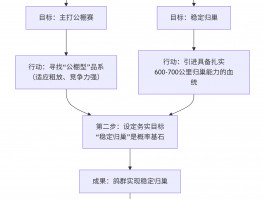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